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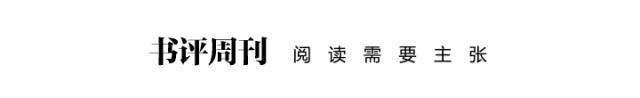
柯文的成名作《在中国发现历史》成书于20世纪70年代。20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柯文的著作正式被翻译引进至中国大陆。1989年,由林同奇翻译、中华书局出版的《在中国发现历史》中译本问世;1994年,雷颐、罗检秋翻译《在传统与现代性之间:王韬与晚清改革》,并由江苏人民出版社出版。在下文中,历史学者、柯文著作的译者雷颐讲述了柯文在中国的接受过程与其学术进路的转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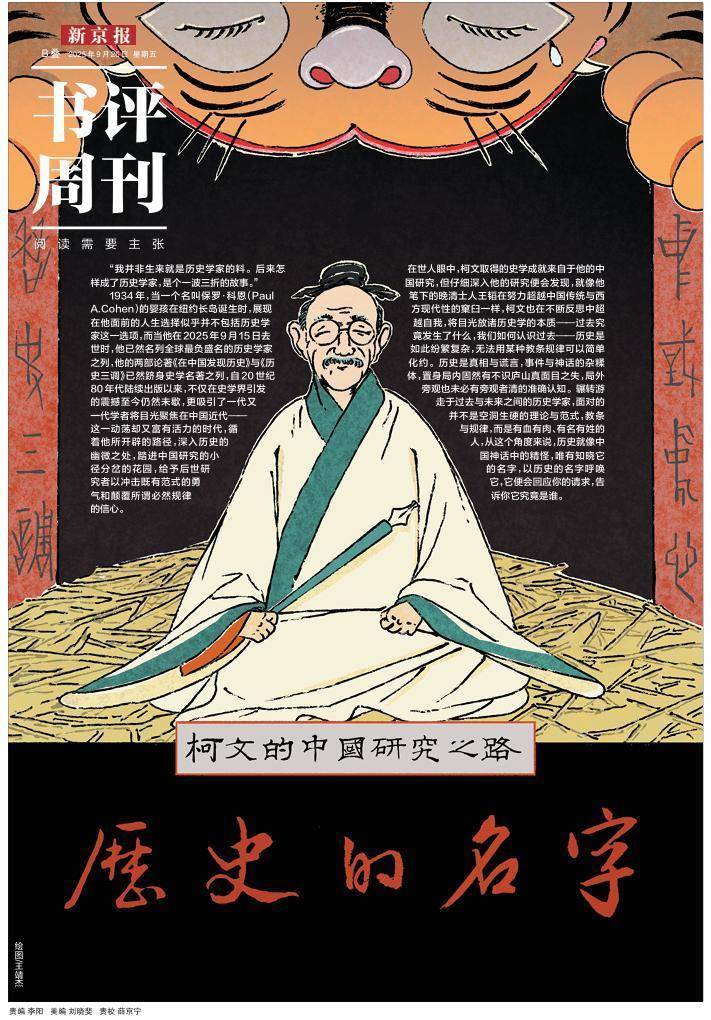
本文内容出自新京报·书评周刊9月26日专题《历史的名字》B04版。
B01「主题」历史的名字
B02-B03「主题」柯文 在中国发现历史
B05「主题」王笛 柯文的批判与传承
B06-B07「文学」保罗·奥斯特 最后一本书
B08「中文学术文摘」青年研究 文摘两则
采写丨李永博
吴光宇作品《卧薪尝胆》(1962),北京画院藏。
柯文的前瞻性
新京报:你是最早一批把柯文的著作翻译介绍给中国大陆读者的学者。当时是出于什么原因接触并翻译《在传统与现代性之间:王韬与晚清改革》这本书?
雷颐:我从大学开始就对外语,特别是英语很感兴趣。研究生毕业后,当时中国的外文著作资源有限,主要集中在外语系和理工科,所以在普通大学图书馆里几乎找不到研究中国近代史的外国学者著作。但幸运的是,我毕业后进入了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所工作。那是国家顶级的研究机构,馆藏里有大量英文、俄文的近代史著作。借此机缘,我在当时读了不少外国学者的书,可以说是如获至宝,阅读得非常兴奋。
但在这些书之间,真正让我震撼的是柯文的《在传统与现代性之间:王韬与晚清改革》。因为我研究洋务运动和中西文化交流,王韬是其中很重要的角色,我自己写文章也常涉及他,所以我认真读完了这本书。柯文不仅研究王韬,也研究了与他同时代的一批知识分子。他的研究方式是通过王韬的经历,进而讨论近代中国的那批知识分子。
雷颐。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所研究员。著有《孤寂百年》《帝国的覆没》等,译有《在传统与现代性之间》等。
最让我惊讶的是,柯文在这本书提出了“沿海与内地”的概念。他认为鸦片战争以后,中国的变革和探索主要发生在沿海地区,而这些探索最终能否落地、能否被朝廷接受,却要由内地来决定。在他笔下,沿海和内地不仅仅是地理上的区分,更是一种经济和文化上的概念。沿海更容易接受新事物,但最终权威和合法性的确立,还要看内地。
我是在20世纪80年代中期读到这本书的,那时正值我国改革开放之初。柯文书里关于沿海—内地关系的分析,让我立刻联想到深圳、广东这些改革开放的前沿地带,和当时现实的情形几乎一模一样。这本1974年写的书,让我感觉像是在1984年写成的,他早在十年前就有如此前瞻的判断,真是了不起!他还提出“从香港到上海”的新文化走廊。晚清时期的王韬等人当时就在这两地之间活动,介绍新思想、新知识。这让我想到20世纪80年代改革开放初期,大量新观念和新鲜事物正是通过香港进入内地的。就在那一刻,我就决定必须翻译这本书。于是,我和同事罗检秋合作翻译了《在传统与现代性之间:王韬与晚清改革》,这也是柯文最早在国内被系统介绍的著作之一。实际上,我认为柯文的这本书非常重要,值得反复阅读,但如今它却被很多柯文的读者忽略。
新京报:当时国内的海外译丛出版刚刚起步,你在翻译的过程中,有没有遇到过挑战?
雷颐:《在传统与现代性之间:王韬与晚清改革》这本书,书名里“现代性”(modernity)这个词,当时几乎没有人用,多数人更熟悉“现代化”(moderniza⁃tion)。出版社也不明所以,甚至劝我改成《传统与现代》,但我坚持保留“现代性”。我还给柯文写信,由此明确“现代性”与“现代化”的区别。“现代化”往往指向的是经济、机器、器物的方面,而“现代性”更多地是指一整套现代的价值观念和思想方式。当时我在翻译这本书的时候,国内知道“现代性”的人非常少,几乎就限定在美学或文学领域。可以说,这本书的翻译,在普及“现代性”这一学术概念方面,也起到了重要作用。
《在传统与现代性之间:王韬与晚清改革》出版后,柯文对我的翻译给予了极高评价,他没有直接对我说,但我后来得知他非常认可我的翻译,这让我非常意外。之后,我又组织参与了“海外中国丛书”的翻译工作,其中包括了周锡瑞的《义和团运动的起源》,我负责统稿和校对。柯文得知后,告诉我他也写了一本关于义和团的书,非常希望由我来译介到国内,当时我正忙于其他事务,于是推荐了杜继东来翻译,并由我来负责校对,这就是后来的那本《历史三调》。
《历史三调:作为事件、经历和神话的义和团(典藏版)》
作者:[美]柯文
译者:杜继东
版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2015年8月
在这个过程中,我特别能够理解严复先生当年说有时候为了翻译一个词要想破脑袋的感觉。《历史三调》的英文书名His⁃tory in Three Keys让我非常纠结。这里的Key是多重含义,既有“钥匙”和“关键”,又有音乐中的“音调”的含义,我在汉语里找不到一个既能涵盖这几层意思,又不显突兀的词。最后我只能翻译成“调”。这多少有点遗憾,因为丢失了“钥匙”“关键”的意涵。但最终《历史三调》这个书名还是被读者接受了。
此外,在柯文的中国接受史当中,他的成名作《在中国发现历史》也很有影响力,这本书挑战了费正清的范式,强调中国历史的内生动力,而不是由外部推动。这本书初版由林同奇先生翻译,他的英语水平极高,而且与柯文有直接交流,翻译得非常贴切又高明。多年后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重版时,柯文还专门请我重新校勘中英文版本,这让我非常受宠若惊。对照之下,我几乎没有改动,反而从林同奇先生的翻译里学到了很多。
学术方法的转向
新京报:你曾在《在中国发现历史》新版序中写道,《历史三调》这本书标志着柯文学术的重要转向。以《历史三调》为分界线,之后的作品与之前有什么明显的区别?
雷颐:从《历史三调》开始,柯文学术方法从之前对史实的考证,转为研究“历史叙事的接受与作用”。《历史三调》不单是研究义和团本身,而是一部史学理论、历史哲学著作,关注“关于义和团的不同叙事”如何影响中国人的历史记忆。义和团其实只是他的一个解决问题的载体、视点;通过“义和团”处理的是个人记忆、集体记忆之间的复杂关系,是历史记忆与现实之间的复杂关系。虽然写的是义和团,但第一部分是历史学家研究、叙述的义和团运动的史实,以叙事为主;第二部分则考察直接、间接参与义和团运动及中外各类人物当时的想法、感受和行为,指出后来重塑历史的历史学家的看法与当时的“当事人”对正在发生之事的看法大为不同;第三部分评述在20世纪初中国产生的关于义和团的种种神话。这三部分,构成了“历史三调”。
《在传统与现代性之间》
作者:(美)柯文
译者:雷颐 罗检秋
版本:中信出版社
2016年8月
沿着这条进路,柯文又出版了《与历史对话:20世纪中国对越王勾践的叙述》,对中国人烂熟于心的越王勾践卧薪尝胆“被神话”的故事,在20世纪中国各个阶段的危机时期,从辛亥革命、民族救亡直到20世纪60年代曹禺的话剧“胆剑篇”,如何不断地通过历史叙事的构建激励人心。
后来,他把这种方法扩展到世界范围,出版了《历史与大众记忆:故事在危机时刻的影响力》,这本书聚焦塞尔维亚、巴勒斯坦、以色列、苏联、英国、中国和法国等国家在20世纪面临的严重危机。为了应对危机,受到影响的民众和国家都在利用那些与现实发生之事有类似主题的古老的历史故事。
批判精神的内化
新京报:你曾说柯文被引进中国的情况有点像福柯或德里达。中国学界对柯文的接受是否有误读或偏差?
雷颐:尽管柯文的学术思想发生过相当重要的变化,但在变化之中,却有不变的部分,就是其深刻的自我反思、批判精神。柯文先生在《在中国发现历史》首版“前言”中写道,他写此书之初,心目中的读者主要是西方特别是美国的中国专家。他想通过这本书,对过往美国的中国研究“提出带有批判性与解释性的估量,以便在同行中引起讨论,借以提高整个领域在进行研究时的自觉性的一般水平。”
如果我们忽视了这种内在的自我反思、批判的精神,就容易把“他者”的自我反思、自我批判变成自己“优越”的证明和资本。遗憾的是,《在中国发现历史》中译本出版后,一部分程度上就是这样被中国学界接受的。这种接受,抛弃了理论的自我反思、自我批判的精神实质,消解了理论的锋芒与革命性。如果说柯文先生有什么值得当代中国学界思考和学习的,就是这种“批判精神的内化”。
本文为独家原创文章。采写:李永博;编辑:何安安;校对:薛京宁。未经新京报书面授权不得转载,欢迎转发至朋友圈。
最近微信公众号又改版啦
大家记得将「新京报书评周刊」设置为星标
2024书评周刊合订本上市!
点击书封可即刻下单
亿配资,股票配资首选门户网站,中股配资提示:文章来自网络,不代表本站观点。